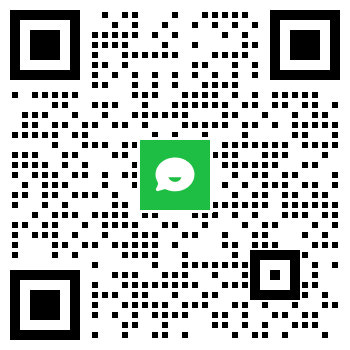文物大盗-卢芹斋民国才是文物损坏、贩卖、流失最严重的时期
当今日我们驻足于博物馆的玻璃展柜前,凝视那些标注着“海外回流”或“原藏于中国”的文物时,总不免心中一痛——那些商周的青铜、盛唐的陶俑、宋元的书画,本应属于这片土地的历史血脉,却成了异国展厅中的“东方奇观”。这一道道文化裂痕的背后,是民国时期触目惊心的文物流失史:战乱中的政府无暇自顾,地方军阀与奸商沆瀣一气,而站在盗卖链条顶端的,正是臭名昭著的文物大盗卢芹斋。
这个被西方捧为“古董教父”的浙江人,在巴黎建起雕梁画栋的“红楼”,在纽约操纵天价拍卖会,将昭陵六骏打碎装箱,把广胜寺壁画整墙剥离。他勾结军阀孙殿英洗白东陵赃物,贿赂海关官员伪造文书,更与欧美博物馆合谋将盗掘称作“保护”。每思及此,恨不能穿越百年时空,将那些被割裂的佛像重新拼合,让打碎的骏马重归昭陵——但历史的伤痕已成定局,我们唯有直面这段血色往事,方能警示未来。
下文将揭开卢芹斋如何编织横跨三大洲的走私网络,如何在欧美权贵簇拥下将盗卖包装成“文化传播”,又如何让50万件中华瑰宝在切割机的轰鸣中永失故土。
卢芹斋(1880-1957)作为20世纪最具争议的古董商人,其文物走私网络横跨欧亚大陆,通过系统性盗掘、跨国贩运、权钱交易及文化营销,将数十万件中国文物非法输送至欧美市场。以下结合其经营手法、重大事件及国际关系网络展开详述:
卢芹斋依托“卢吴公司”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文物收购网络,分号设于北京、上海、西安等文物重镇。他与盗墓团伙、军阀(如孙殿英)及故宫太监勾结,形成“盗掘-收购-洗白-出口”产业链。例如,孙殿英盗取慈禧陵墓后,卢芹斋通过伪造“仿品”标签,将翡翠西瓜、夜明珠等珍宝走私至美国。此外,他通过贿赂地方官员,获得伪造的“合法”通关文件,如昭陵六骏出口时便利用了北洋政府的通关证明。
为规避海关检查,卢芹斋采用暴力切割(如龙门石窟佛像)、分装运输(如将昭陵六骏打碎装箱)等手段。大型壁画(如山西广胜寺元代壁画)被整墙剥离后分割成数百块,以“艺术品零件”名义报关。其纽约分店负责人弗兰克·加罗(Frank Caro)负责对接美国海关,通过政商关系疏通渠道,甚至利用外交豁免权运输文物。
二、欧美市场的文化营销与拍卖操控
1926年,卢芹斋在巴黎第八区建造中式“红楼”,内部陈列来自中国的石窟雕像、漆画壁板及古典家具,地下一层仿照魏晋石窟设计,被西方称为“中国卢浮宫”。红楼不仅是文物仓库,更是文化沙龙,定期举办特展吸引藏家。例如:
1933年“西伯利亚艺术展”展出商周青铜器与高棉雕塑;
1936年“汉代砖陶明器展”推出墓葬陶俑;
1940年“中国石雕展”展示龙门石窟切割佛像。
这些展览配合其出版的《中国石雕展》《唐宋元绘画》等图录,将文物包装为“东方艺术瑰宝”,极大抬升市场价值。
卢芹斋1915年于纽约开设分店,利用美国经济腾飞期的收藏热潮,与洛克菲勒、摩根家族建立长期合作。他主导的两次纽约拍卖会(1920年代)售出2800余件文物,成交价仅10余万美元,但后续通过博物馆捐赠抵税、学术研究背书等操作,使文物价值飙升。例如:
元代白瓷观音像以300大洋(约45美元)购入,后以50万美元售予大都会博物馆;
宋代白瓷碗国内进价10大洋(1.5美元),转手售价1万美元。
此外,他资助宾夕法尼亚大学、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的“中国艺术研究项目”,换取学者为其文物出具“学术认证”,形成利益闭环。
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:购得昭陵六骏中的“飒露紫”“拳毛騧”(12.5万美元)及响堂山石窟雕塑;
大都会艺术博物馆:藏有其经手的广胜寺壁画、李公麟《华岩变相图》及商代青铜方罍;
波士顿美术馆:收购龙门石窟石狮、隋代青铜造像及汉代画像砖;
纳尔逊-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:获得山西广胜寺《药师经变》壁画。
这些机构通过卢芹斋批量采购文物,仅1926年上海港文物出口关税即达77.8万海关两(约合等值美元),占当年中国文物外流总量的半数。
卢芹斋与约翰·小洛克菲勒合作,将清宫旧藏青铜器以“慈善捐赠”名义抵税;为J.P.摩根家族定制“中国皇室珍宝”收藏系列,包括唐代金器与宋代官窑瓷器。其信件显示,他常以“中国政府禁止出口”为噱头,向富豪客户渲染文物稀缺性,例如向弗利尔美术馆推销时强调:“这是最后一批能合法离开中国的珍品”。
昭陵六骏:为运输便利,将石刻打碎,导致“飒露紫”马鞍断裂、“拳毛騧”腿部残缺;
龙门石窟《帝后礼佛图》:切割浮雕时使用炸药,造成石窟结构永久性损伤;
响堂山佛像:盗凿头部与躯干分离,部分雕像因运输颠簸碎裂。
卢芹斋利用国际法漏洞,以“私人收藏”名义规避文物原产地保护条款。他曾在纽约召开记者会,污蔑竞争对手的商代青铜兵器为“仿品”,迫使对方低价抛售。其自辩称文物“在西方免于战火”,但内部文件显示,他刻意利用二战期间中国文物保护真空期加速走私。
据保守估计,卢芹斋经手文物超50万件,涵盖青铜器、佛教艺术、书画、玉器等门类,占1949年前流失海外中国文物的一半。其上海分店1949年被查封时,一次性收缴342件文物,包括春秋晚期牲尊(现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)。
在西方,他被尊为“中国艺术启蒙者”,推动欧美博物馆建立亚洲艺术收藏体系;而在中国,他被斥为“文化叛徒”,导致大量文物本体损毁与历史语境断裂。其晚年虽捐赠战国青铜器“嗣子壶”给清华大学,并参与抗日募捐,但无法抵消其行为的原罪性。
卢芹斋的案例揭示了殖民时代全球艺术贸易的掠夺本质,其商业帝国建立在近代中国的动荡与文化遗产管理缺失之上。尽管部分文物因外流得以保存,但其非法性与破坏性始终是民族记忆的创伤,至今仍为跨国文物追索的难点。
六、卢芹斋的个人生活:矛盾婚姻、家庭操控与文化割裂
卢芹斋的私生活与其文物帝国密不可分,其复杂的家庭关系、跨国婚姻及对后代的刻意疏离,折射出他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扭曲身份认同。以下从婚姻、家庭操控、社交野心及后代命运四个维度展开:
畸形的婚姻:妻子、岳母与情人三位一体
1910年,卢芹斋在巴黎与帽子店店主奥尔佳(Olga)之女玛丽·罗斯(Marie Rose)结婚。当时玛丽仅15岁,而卢芹斋30岁。这场婚姻本质是利益交换:奥尔佳作为寡妇,急需经济依靠,而卢芹斋渴望通过法国家庭获得社会地位。婚后,玛丽沦为名义妻子,卢芹斋与岳母奥尔佳长期保持情人关系,三人同住巴黎蒙梭公园附近的豪宅,形成畸形家庭结构。
奥尔佳凭借法国国籍与社交手腕,成为卢芹斋商业帝国的实际掌权者。她不仅持有公司保险箱密码,还负责与法国海关、税务部门周旋。1926年建造“红楼”时,奥尔佳亲自监督建筑预算,甚至要求将部分文物销售款存入瑞士私人账户。卢芹斋在信件中抱怨:“她(奥尔佳)像看守宝藏的龙,连一枚铜板都要嗅三次。”
卢芹斋与玛丽育有四个女儿(1920年代出生),但她们均被刻意隔绝于中国文化之外:
语言隔离:女儿们仅学习法语、英语,卢芹斋禁止家中使用中文;
身份隐瞒:对外宣称女儿们是“中法混血”,掩盖其华人血统;
婚姻安排:长女嫁法国银行家,次女联姻比利时贵族,试图彻底融入欧洲上流社会。
卢芹斋曾对友人叹道:“我没有儿子,这些女儿终究是别人的。”
巴黎“红楼”:社交野心与文化表演
1926年落成的巴黎红楼(29 Rue de Courcelles),是卢芹斋打造的个人纪念碑。这座中式建筑混搭了明清王府、藏式佛堂与法式沙龙:
一层陈列青铜器、佛像,用于接待政商名流;
二层仿紫禁城寝宫,摆放拔步床与苏州刺绣,实为文物仓库;
地下密室仿敦煌石窟,藏匿未报关的壁画与石雕。
卢芹斋常身着长衫,以“东方贵族”姿态在此举办晚宴,宾客包括法国总理赫里欧、日本驻法大使杉村阳太郎等。
奥尔佳母女不仅是家庭成员,更是卢芹斋的“文化展品”。他要求玛丽在沙龙中身穿旗袍表演茶道,而奥尔佳则扮演“中国艺术权威”,向客人讲解文物掌故。1935年《巴黎画报》记载:“卢夫人(玛丽)像一只精美的瓷瓶,被摆放在红木条案上,微笑如同定制的面具。”
二战期间,卢芹斋将部分资产转移至瑞士,导致与奥尔佳关系恶化。1948年奥尔佳携女儿们搬离红楼,仅留卢芹斋独守空楼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这座楼里每一块砖都刻着贪婪,连老鼠都在啃噬我的良心。”
1957年卢芹斋病逝前,曾试图让孙女学习中文,但遭女儿们拒绝。他托人将一枚战国玉璧送回湖州老家,附信写道:“此璧出自楚墓,与我同乡同源,望埋于祖坟旁。”但因中法断交,玉璧最终流落纽约拍卖行。
卢芹斋的孙女在2010年法国纪录片《卢芹斋之谜》中坦言:“家族从未保留任何中文物品,母亲(玛丽)临终前烧毁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信件。” 四女的后裔至今拒绝承认华人血统,其曾孙女甚至将“卢”姓改为“Loo”,彻底抹去中国印记。
卢芹斋一面在西方扮演“东方文化大使”,一面在家族中践踏中华传统,这种撕裂源于其阶级跨越的焦虑:
自卑与虚荣:出身仆役的他,借文物与豪宅伪装贵族身份,却在欧洲精英眼中仍是“高级掮客”;
文化背叛:他深知文物承载的民族记忆,却亲手将之拆解为商品,正如他将家庭拆解为利益工具;
历史报应:其子孙的文化断根,恰似那些流落海外的文物——失去故土,沦为无魂的装饰品。
正如学者王鲁湘所言:“卢芹斋的红楼是他毕生野心的实体化,每一件文物都是他垫高自我的砖石,但垒得越高,越显出其灵魂的矮小。” 这段畸形家史,与其文物倒卖网络一样,成为近代中国悲剧的微观缩影。
记录生命的瞬间📷 不走寻常路线✈️ 远离烦人的驴马烂子🎧 让内心获得平静🤟🏻
版权声明:本文由网络蜘蛛自动收集于网络,如需转载请查明并注明出处,如有不妥之处请联系我们删除 400-0123-021 或 13391219793